
2022年12月2日晚,由华东师范大学诠释学研究所、“中国诠释学”上海市社科创新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涵静书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的“诠释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一期)”第四讲《文本概念的哲学诠释学解析》于线上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山东大学傅永军教授主讲,广西大学黄小洲副教授主持,两百多位师生于线上共同参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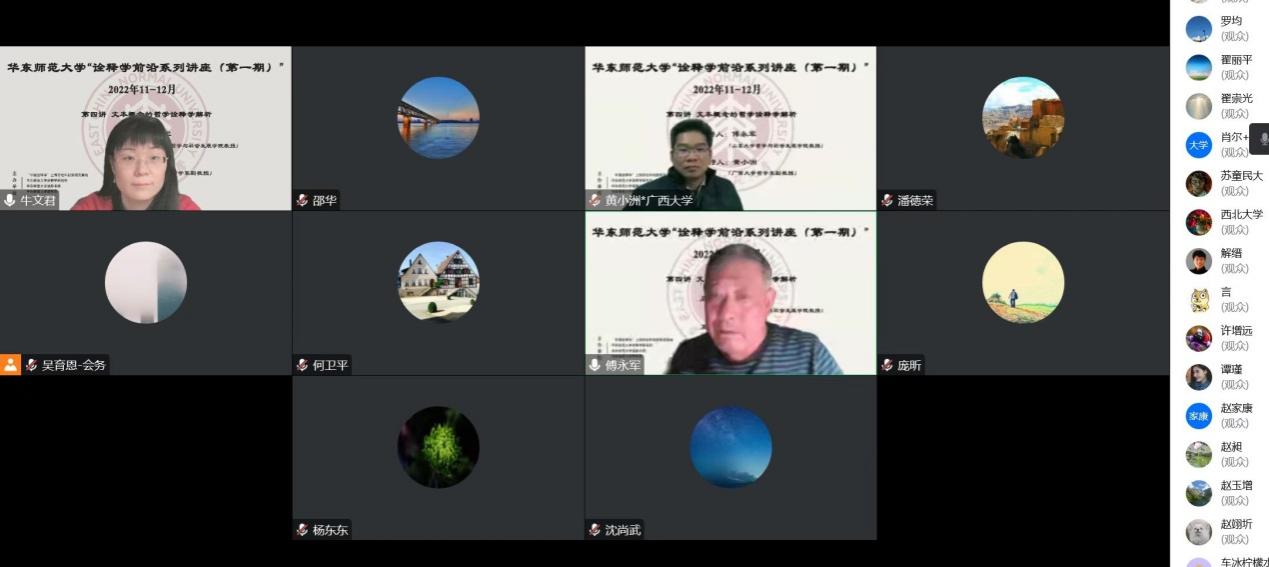
讲座伊始,傅永军教授首先强调,本场讲座的关键词——“文本”,是在哲学诠释学本体论转向的背景下被讨论的。自诠释学完成了从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转变,“文本”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哲学诠释学不再被单纯理解为解释的艺术——帮助人们克服阅读特殊文献的困难,也不再被视为人文科学的纯粹方法论。哲学诠释学关注的是理解问题本身,探究理解成立的条件,由此成为一种理解之学。
通过转向理解,语言、思想、存在三者同构,哲学诠释学关注存在问题,而存在问题又以文本诠释的方式出现。所以,对哲学诠释学“文本”概念的理解必须立足于其本体论转向,立足其所建构的语言、思想、存在的三位一体结构。

接下来,傅永军教授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对哲学诠释学中文本概念意义的探究:
1.文本概念何以成为哲学诠释学的中心概念。
2.哲学诠释学如何理解文本概念。
3.文本基本特征的哲学诠释学剖析。
在“文本概念何以成为哲学诠释学的中心概念”这一部分,傅永军教授选择以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与语言密切的关系为切入点展开讨论。哲学诠释学的出发点是理解存在的语言性以及这种语言性和存在之间的关系。当我们将语言性看作是诠释对象以及诠释过程的规定性时,诠释学就将自身的普遍性反映在被理解对象的存在状况上,即,对象以语言的方式存在。那么,以语言为中介能把理解和世界联系起来吗?或者说,是语言使得思想与存在在其原始的依附关系中被表现的吗?
伽达默尔通过对语言哲学的历史检视对这一问题做出了回答,他批判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传统的、主流的语言哲学将语言与事物相分离的观点,返回到德国古典语言哲学。
“语言与存在之间并不具有真正的关联”这种观点可以进一步被区分为约定论的与自然主义摹写论的。约定论认为,语言本身没有任何内容或意义,它的意义来自人的命名与赋予,因而语言仅仅是一种工具,这样的观点很容易造就人工语言的思想;自然主义摹写论相较于约定论,强调语言和事物之间的一种图像关系,人使用语言描述事物必然要求按照语词与事物的对应关系进行。
伽达默尔对以上两种观点进行了总结:首先,约定论与自然主义摹写论都认为事物先于语言。人们在绝对无言中得到事物的知识,然后才有语言。在这一点上,二者的差别在于,约定论认为,我们先理解事物然后约定一个语词指称它;摹写论认为理解事物之后,人们找出适当的语词匹配事物。其次,约定论与摹写论都认为语言和事物是两种不同的存在,事物不是语言性的。最后,二者都将语言理解为一种工具,事物与语言处在完全分离的状态中。
伽达默尔将这种思想进路归结为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经由中世纪共相之争,再到近代康德对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结合,最终抵达逻辑证实论与语言分析哲学的语言哲学道路。这条道路错误地理解了语言的功能,因此他主张寻找另外一条语言哲学道路。
第二条道路是由希腊化-罗马时期的修辞学传统与基督教的逻各斯神秘主义开始,经由文艺复兴时期但丁的人文主义与维柯主张的新科学,直到最终综合于从赫德到洪堡特再到米德的德国古典语言哲学的道路。这一条道路与上一条是相反的,它不是仅将语言理解为工具,而是认为语言最重要的功能就在于开显世界。
傅永军教授将后一条语言道路的特征总结为四个方面:
1.语言不是科学借助理性逻辑对事物进行独白式的思考的工具、单纯的指示性符号系统。
2.语言是沟通的媒介,与事物内在一致,语言的功能主要在于开显世界与事物。
3.一切可以成为对象的东西都在语言中,并且能够成为被意识到的对象必须是语言性的。
4.语言观就是世界观,人拥有什么样的语言就拥有什么样的世界观。
伽达默尔认为,我们要在这后一条道路中重构语言与存在之间的关系:首先,凡是可理解的都在语言范围内,不能被语言言说的事物永远隐藏而不存在,存在就是在语言中存在。其次,语言是开显事物的真正中介,语言的源初品格就是让事物出现在自身之中而自身隐没。最后,语言、思想、存在之间必然存在着一种本体性的结构关系,思维与言说始终是关于某物的思维与言说,存在总是语言性的并因之而成为可理解的。
语言呈现存在,存在被语言说出的就是思想,说语言就是去思想,去思想就是用语言说存在。语言和存在的这种必然的紧密性,伽达默尔称之为“语言的事实性”。语言的事实性使存在必然呈现在言语中,人可以像阅读书籍一样“阅读”存在。此时,诠释学便具有经典诠释学的典型品格,人们就可以像诠释文本那样对存在做出诠释,这就是存在的文本化。由此,文本概念必然成为哲学诠释学的核心概念。
在澄清了“文本”如何成为哲学诠释学的中心概念后,傅永军教授进一步对“文本”进行了界定,由此进入第二个问题——哲学诠释学如何理解文本,这一部分以对语言学意义上对“文本”概念的理解进入到哲学诠释学的“文本”概念为思维进路展开。
傅永军教授首先介绍了语文学意义上的文本概念:文本是语言的一种实际运用形态,根据一定的语言衔接和语义连贯规则组成整体性语句系统,这个语句系统在一定语境中被作者选择并赋予某种意向以此向读者传达某种意义。因此,文本就具有三方面的条件:作者、作者在某种语境中以某种特殊方式选择并排列符号、意图向特定语境中的读者传达某种特殊意义。此外,文本还具有五个因素:作者、符号、语境、读者、意义。
那么,在语文学层面上的“文本”就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文本是一种自身包含着意义、由一系列语句串联而成的连贯序列,它自身构成一个相对封闭、自足的系统;第二,文本是作者意图的存在方式,它先于诠释者的理解而先行存在,是理解和解释受阻时所要回归的东西;第三,文本的意义不是作者的主观意识,而是作者意识到的事物以及他处理意识到的事物的方式。对文本意义的诠释不是还原作者的心灵史,而是以与作者相同的方式与态度去阅读文本;第四,生活世界中语言性积淀下来的世界经验对于理解文本以及通过文本理解理解者完成自我理解的功能严重被忽视,诠释需要方法、技巧,诠释不过是对文本进行科学解释的基础。
这样一种文本概念的缺陷在于,作者在完成文本时,已经将读者的主体性排除在外,读者只需要进入作者的精神世界中、配合作者的意向就能理解作品。这种定义严重轻视了诠释和诠释者,并不真正关心文本,甚至也不关心作者,只关心阅读所产生的意识活动、认知能否在文本那里得到验证,这是一种对他者存在的蔑视,并不能将诠释活动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实现出来。因此,必须要扬弃语文学的文本概念进入到诠释学的文本概念。
顺着伽达默尔的思路,如果要摆脱语文学的文本概念进入到诠释学的文本概念之中,就要进入到现代语言之中。文本进入现代语言有两种方式,一是文本作为布道和教会学说进行解释的文献,将《圣经》中的真理阐发出来;二是自然使用的文本概念,主要在音乐之中,表现为歌唱艺术的文本,是对词语的音乐解释的文本。在此意义上文本不是先行给予的东西,而是从歌唱实践过程中积淀下来的东西,即文本在长期不断地进行理解和解释中形成。
相应于文本的两种历史存在方式,文本的成立具有两个基本要求:相应于第一种历史存在方式,文本必须在经典意义上加以定义,只有具有经典性与真理性的东西才能被称为文本;相应于第二种历史存在方式,文本必须在诠释中生成,它不是先于诠释的先行给予物,只有在诠释中生成并能无限延展意义的东西才能被称为文本。
随后,傅永军教授通过阐述对文本概念两个内在规定性的进一步理解使得其在哲学诠释学中的意义更加明晰。第一,不能将文本解读为存在物的现成状态,而是要将其解读为指向存在于语言中的存在物的真理,或者说事情本身。文本的经典性和真理性这个内在规定性指明文本就是诠释的对象,诠释指向文本的意义,由此便杜绝了诠释的相对主义。第二,诠释的对象是文本的意义,但意义永远不会被完全凝固在文本中,成为某种具有直接性和所与性的存在物。文本意义的无限延展性这个内在规定性指明文本是一种语言诠释的生成物,是一种可以被带入不同语境中被不断地赋予新言说的语言意义整体。
最终,文本的这两种内在规定性在诠释中得到了统一,文本被诠释者带入不同语境之中,将事情本身带入事情本身所遭遇的不同语境之中,达到多样性的表现,这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说的“一与多的关系”。
在最后一部分,傅永军教授对哲学诠释学中文本概念的基本特征进行了剖析。他指出,在诠释学本体论转向下的文本概念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历史性、非成品性与可读性。
文本的历史性是指文本概念是一个生产性的概念,它不是在诠释前或理解之外预先存在的东西,而是理解和诠释生产出文本。
文本的形成与诠释者相关,也与文本作为流传物的历史规定性相关。文本必须由诠释者和被诠释者的诠释过程形成,这一过程能完成是因为视域的融合。这就意味着,在进一步分析文本的历史性时,必须注意文本在被诠释者带入诠释之前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而可能性的文本也带有自己的视域,因此更源初的视域是可能成为文本的东西的视域是历史性地存在的。
同样,文本的历史性使我们意识到了自身的有限性特征,人们是在理解文本的历史性中历史地将通常以文本方式存在的被理解物再文本化的。历史性既是文本的“即是”状态,也是文本的“将是”状态。
文本的非成品性是指文本不能在诠释前先行给定,它只能在诠释中成为理解的对象。文本是单纯的中间产品,是理解事件中的一个阶段。
作为一个阶段和一个诠释学意义上的半成品的文本,其意义指向两个方面:强化文本与诠释之间的诠释学联系;强调突出文本理解中“一与多”的辩证法。在诠释过程中,我们是向着诠释中的真理而展开诠释的,对“一”的理解总是奠基在先行具有中,对它的解释要奠基在先行视见,“一”是历史性存在的“一”。
可读性不是语文学层面的概念,而是一个哲学概念。文本的可读性揭明诠释者必须能够在阅读中让文本的意义去除遮蔽而如其所是地开显出来。可读性意味着文本成为诠释的对象,阅读者能在自己的诠释行动中将文本的意义呈现出来。
诠释学的宽容、善意原则——相信文本具有可读性的善意,是保证文本可读性能够得以实现的诠释学形而上学原则。并且,必须在诠释者与文本所构成的诠释学关联中文本的可读性才具有场域。

最后,傅永军教授提到了伽达默尔对文本的理解与康德的对认识对象的阐述的接近性。康德认为,认识对象是经由主体的先验综合所造就的、在先天形式下得以规则性联结所形成的表象整体。就此而言,认识活动发动之前不存在认识对象。伽达默尔认为,某种存在物,在没有被诠释者纳入诠释过程之前,它不是文本,只有当其进入诠释过程中被实际地解读时,它才能成为完全的文本。这是一种建构的活动,但不是康德式先验的构造活动,而是一种在“我与你”关系中展开的对话活动。颇有趣味的是,伽达默尔从反观念论出发却无意实现了观念论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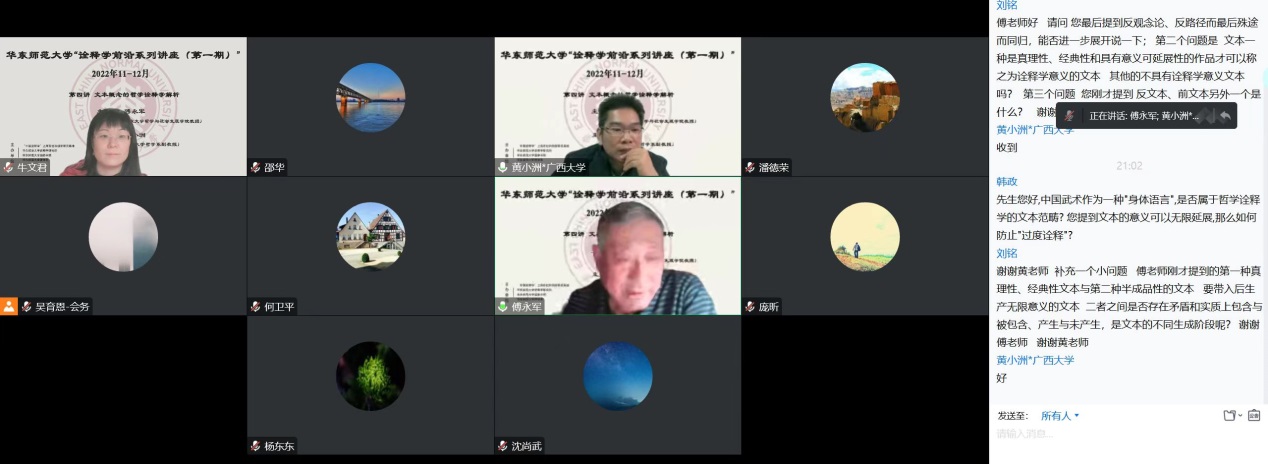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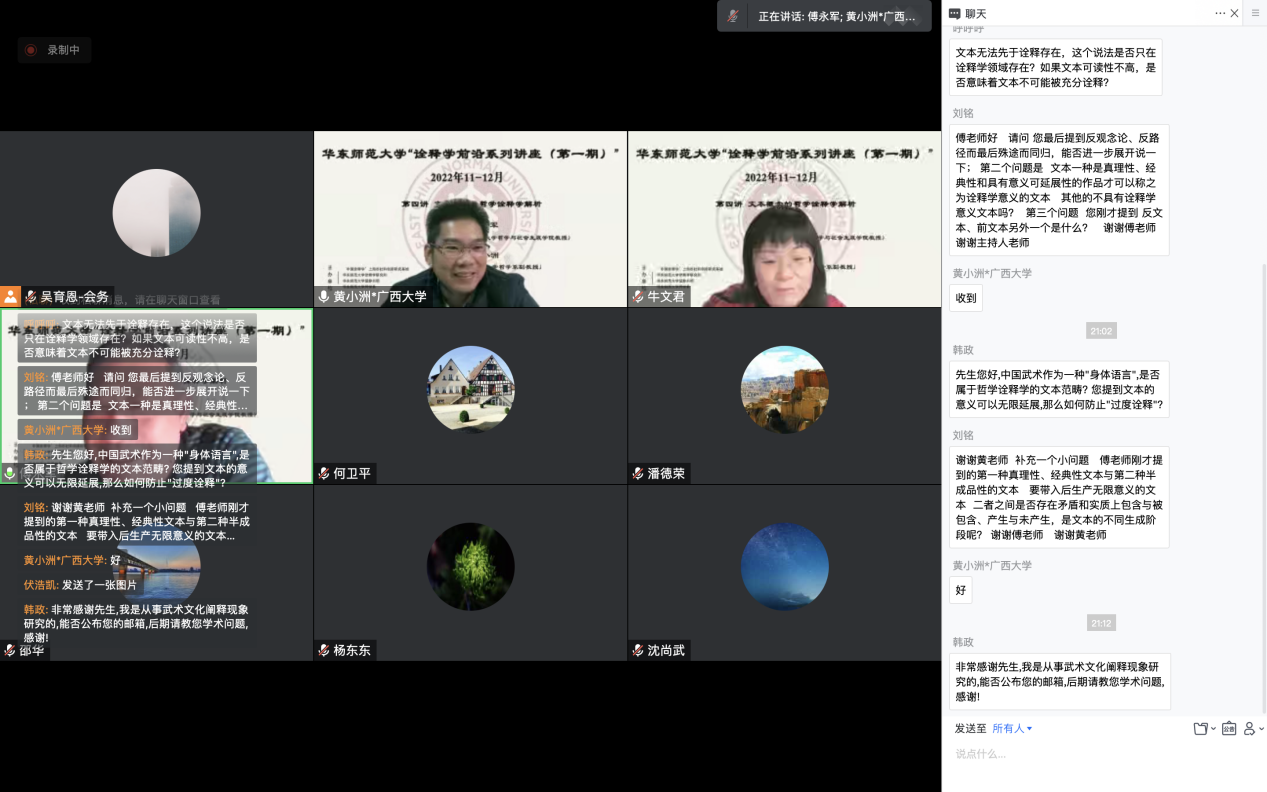
在随后的问答环节中,傅永军教授也对这一问题做出了更进一步的回答。他认为,哲学诠释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对峙就在于一个强调纯粹理性,一个强调历史理性。纯粹理性关心的是在自身中如何实现合法性的原则,而不关心理性遭遇的语境,语境被视作带来主观性、片面性的因素。哲学诠释学关心理性在处境中的使用,关心理性在处境中遭遇的偶然性、主观性,关注理性使用者的生活经验是否对他的理性使用产生影响。
本次讲座在热烈的问答环节中圆满结束。
(撰稿:吴育恩)

 学校主页
学校主页 校内链接
校内链接 校外链接
校外链接 校内邮箱
校内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