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2月18日晚,由华东师范大学诠释学研究所、“中国诠释学”上海市社科创新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涵静书院、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联合举办的“诠释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一期)”第六讲《“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于线上顺利举行。本次讲座由安徽师范大学彭启福教授主讲,山东师范大学杨东东副教授主持,两百多位师生于线上共同参与、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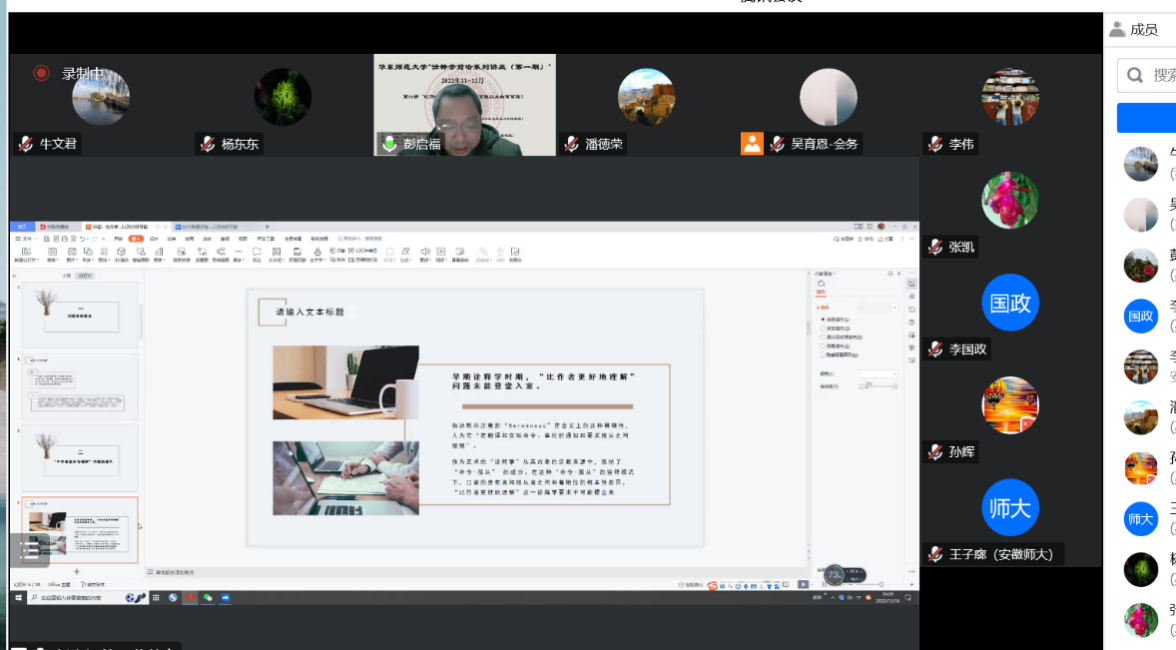
本场讲座以对“比作者更好地理解”这一诠释学话题概念史的追溯为线索展开,彭启福教授对该问题的问题域进行了廓清,梳理了从马丁·路德到浪漫派诠释学等思想家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论述。
彭启福教授首先指出,在早期圣经诠释学“命令-服从”的诠释模式下,由于口谕的发布者和服从者有着地位的根本性差异,故而不可能提出“比作者更好地理解”这一诠释学要求。直到宗教改革时期,路德提出“圣经自解原则”,以瓦解罗马教会对释经权的垄断,不过,这一诉求在路德那里仍未真正被提出,只是出现了萌芽。
其次,彭启福教授谈到了康德与费希特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曾明确肯定“比作者更好地理解”是可以实现的,尤其是在作者未能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情况下。彭启福教授指出,康德敏锐地觉察到了作者内在思想与外在表达之间的诠释学问题。费希特在讨论“卢梭关于艺术与科学影响人类幸福的主张”时站在学者阶层的立场,对卢梭的行为与其主张的差异进行了批评,并提出了解决矛盾的方法,费希特的批评分为“一隐一显”两个方面:显性的方面指向无意识层面,对这一层面的揭示,正是费希特断定他能比卢梭更好地理解他自己的根据所在;隐性的方面是费希特将卢梭的基本原理与行为放置在他所处的历史条件、社会状况中,考察其行动的深层原因。

接下来,彭启福教授梳理了浪漫主义诠释学关于“比作者更好地理解”的主张。施莱格尔的《文学与诗断片》《雅典娜神殿断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述。他指出,“为了理解某个对自己也只是一知半解的人,就必须首先透彻地理解他,超出他对他自己的理解,然后却还要像他本人那样一知半解地来理解他。”施莱格尔的回答把讨论的重心由作品转移到作者,对作者的理解成为对作品理解的重要步骤。施莱尔马赫在1819年的《诠释学讲演》中明确提出“比作者更好地理解”这一任务,他认为“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自己”有两个前提性、基础性的条件:第一,从“作品本身”出发;第二,追寻作者的“有意而为”。以上两个要求似乎只涉及到“与作者同样好地理解”,它过渡到“比作者更好地理解”还需要更进一步,也就是达到作者尚未意识到的无意识的层面。彭启福教授将施莱尔马赫对“比作者更好地理解”的理解模式归结为“由文入史,由史入心”,在对话语、语言、精神三者之间的关系做历史考察的基础上,进入到对作者心理过程及其对作者影响的把握。

施莱尔马赫的弟子伯艾克,提出四条解释原则,发挥了“由文入史,由史入心”的理解路径。在《语文科学的百科全书和方法论》一书中,伯艾克提出语文学诠释学方法论的四条解释原则:(1)语法解释;(2)历史解释;(3)个体解释;(4)类型解释。前两条是“基于被传达信息的客观条件的理解作出的解释”,后两条是“基于被传达信息的主观条件的理解而作出的解释。”伯艾克将历史解释视作语法解释的必要补充,但历史解释的适应性不能超过语词的语法含义所允许的范围。“基于被传达信息的主观条件的理解而作出”的个体解释与类型解释是对“由文入史,由史入心”路径的进一步推进。
彭启福教授指出,尽管伯艾克与施莱尔马赫的理解路径存在着细微的差异,但是他们更好地理解都视作着更多的理解,而同样的理解都指向对作者真实意图的理解。
在讨论环节,众多老师、同学纷纷向彭启福教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在这一环节,彭启福教授也对伽达默尔从本体论立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作了简要介绍。本体论诠释学澄明理解如何发生,其中产生的“视域融合”也适合于被表达为“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的话语”。在伽达默尔所倡导的文本的不同理解的背景下,或许只有在理解中体现出实践智慧,结合诠释学处境对文本进行富有时代价值和意义的理解,才可以谈得上“比作者更好地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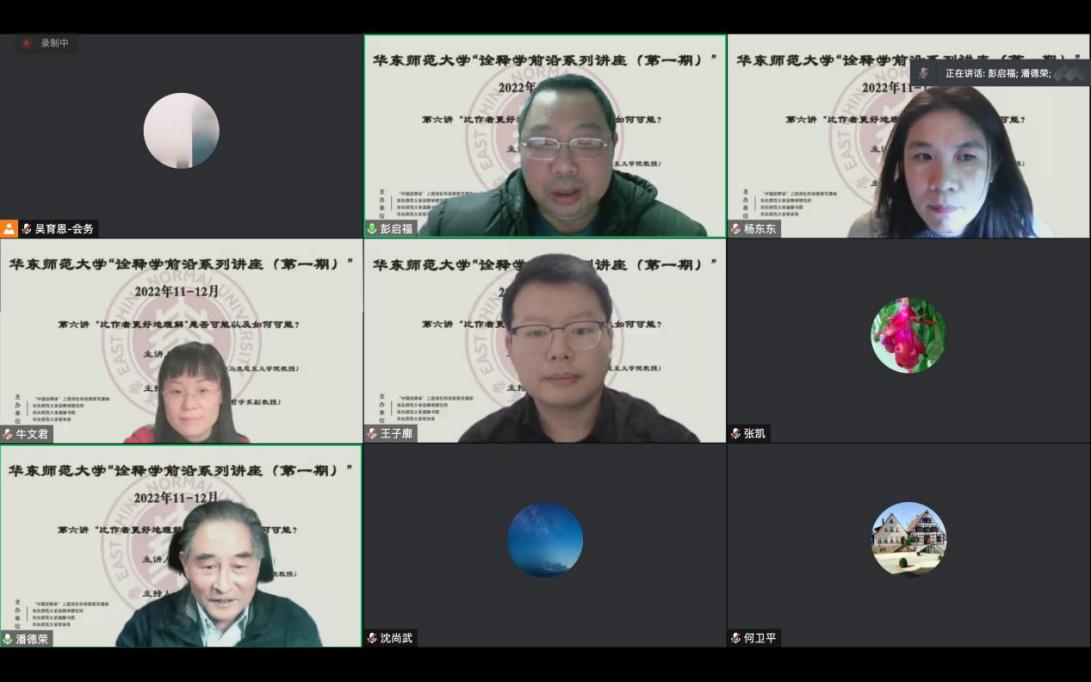
最后,潘德荣教授对整个系列活动的六场学术报告进行了总结发言,华东师范大学诠释学前沿系列讲座(第一期)圆满落下帷幕。
撰稿:吴育恩

 学校主页
学校主页 校内链接
校内链接 校外链接
校外链接 校内邮箱
校内邮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