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动回顾 | 知识与行动的第一人称视野——安斯康姆《Intention》导读
2020年5月13日下午三点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阅读季之经典原著导读活动2020年第三场在“腾讯会议”云端举行。本次活动特邀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徐竹副教授导读安斯康姆的《intention》。哲学系、教育学部、数学科学学院等近百名学生参加,活动由哲学系学生联合会学术部副部长蔡添阳主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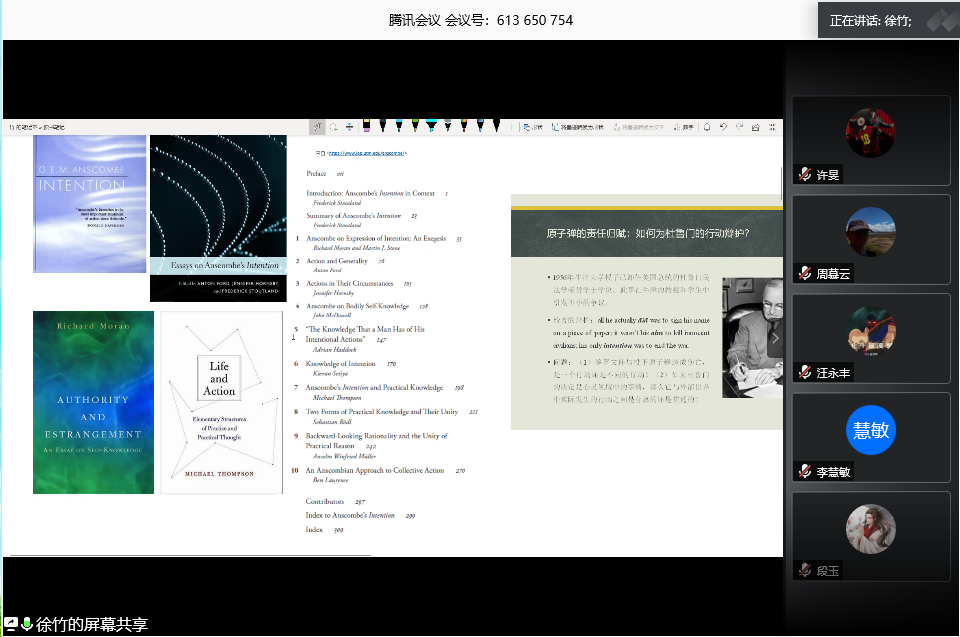
背景介绍
徐竹老师介绍说,安斯康姆是牛津哲学界的代表,她的哲学理论有两个主要来源,其一是作为天主教徒,有天主教哲学的传统,其二是作为维特根斯坦的学生,对维特根斯坦文本的解读、翻译和编撰,这两个传统在《intention》这本书里都有体现。安斯康姆的哲学贡献除了对维特根斯坦的解读之外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他的伦理学、其二是对行动哲学的推动。这本著作就引领了行动哲学的当代复兴。
这本书的写作有一个背景——原子弹责任的归赋:牛津大学要授予杜鲁门一个学位,由于原子弹事件,很多人质疑杜鲁门获得学位的资格,因此展开了关于意图和行为责任的讨论。安斯康姆便开始思考行动的意图或意向性行动如何界定的问题。
对于这本书的译名,有“意向”和“意图”两种,徐老师更认同“意图”的译法。他阐释道:前者的译法存在问题,intentional的范围比intention宽泛,包括各种类型的欲望,行动哲学讲到的是与行动相关的intention。而当你决定做某事时,必须在深思熟虑之后确定一个自己的意向对象作为自己的意图。
内容概略
徐竹老师认为这本书有两个背景观念,一是区分意向对象和物质对象两个层面,二是关于自我知识安斯康姆认为,它一定是和身体相关的,因为行动者对行动有自我知识与否,是可以有规范性标准去评判的,所以可以是真正的知识。
徐老师对文本进行了划分,分为五个单元:(1)怎样界定意向性行动的问题,(2)意向性行动的描述和表达,(3)核心论证即行动者对自己行动的理解构成实践(非观察性)知识,每个人对自己的行动有一个第一人称的特殊把握,(4)具体的话题:现代的道德哲学对实践推理存在误解,(5)回到主要的问题。接下来徐老师通过几个核心段落的分享来做概略性的工作。
第一单元
提出问题:我们界定意向性行动的理由和标准是什么?安斯康姆认为why问题(你为什么做此事情)可以适用于这种行动的界定,若没有原因,说明这不是意向性行动。但这个界定尚需完善,对于why问题的回答包括原因,原因不全是理由,为了收缩标准,安斯康姆提出“非观察性的知识”的概念,即不由观察而获得的知识(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样做)就是意向性。作者接下来又提出一些限定条件:要排除对于肢体位置的知识和关于心理的原因的知识(如鳄鱼案例,即是我诉诸于心理的原因而自己对行为的解释,不是意向性行动)。这样得到了最精致的意义上的why问题的回答,意向性行动的界定就比较清晰了。
第二单元
第二部分的工作是进一步暴露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例如我在朝一个屋子里泵水,来毒害屋子里的人,因为可能里面的人是纳粹党的成员,他们在密谋害人,毒死他们我就能拯救很多人的生命。泵水的人的行为包括肌肉运动等生理运动、可识别的节奏等,其行为过程有很多描述的途径,但他做的很多事都不是他的意向性行动。回到的意向对象和物质对象的区别,意向性的标准是和我的描述符合意向性对象的时候这个活动才是一个意向性活动。
第三单元
徐老师认为这部分强调行动者对行动的第一人称的认识的特征,就是不由观察而知道。我无意间按响了铃铛,我对这个行为实际上没有非观察性知识;反之如果我有意图做某事,则我不需要观察。意向性知识知识一定是第一人称上的,非观察性的。徐老师进一步澄清了意向对象与物质对象的关系,两种对象不一定相吻合,作者认为外在观察下发生一个物理事件是happen,而从第一视角看就是doing,以此来统合二者。但作者又否定了这个结论,在闭着眼睛写字的案例中,体现了观察性知识和非观察性知识的对立,意向对象和物质对象背离。但是这又导致了新的问题,现代的知识概念认为信念要符合事实,即物质对象的层面,不符合事实的信念怎么可能是知识呢?他又提出了购物清单案例,即考虑清单和记录的区别时,就可以澄清:意向性行动知识不会被事实证伪,不必要符合物质对象,也不会因此被认为不是知识。因此他提出了实践知识,这种意图的非观察性的知识就是实践知识,现代性的知识直有思辨的知识,他要求回到实践知识。
第四单元
实践知识讲的概念可类比于命令,意图就是自己给自己的命令,这样在现代性的标准型实践知识就不是知识,作者认为现代知识领域已经没有实践知识的余地了。他回到它的天主教传统,其实践知识这个概念来自阿奎那,阿奎那区分了实践知识和思辩知识,前者是对象的原因,后者导源于对象。他认为现代性下实践的推理,亚里士多德的实践三段论的核心现在已经非常模糊了,三段论的推理过程被看成演绎来处理的,作者认为这样理解实践推理时一种误解。亚里士多德关于实践推理意思时“结论即行动”。演绎得不出这么强的结论,除非加强大前提,然而实践推理没有那么强的普适性。现代有些人认为我们可以把行动者的愿望作为大前提,但这样没有了行动者的筹算。因此还要回到意向对象和物质对象的区分才能理解,大前提的起点是意向对象,而不是物质对象,澄清这个才能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推理原意。
答疑与互动
讲座最后同学们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徐老师也做了详细的解答,以下为节选:
提问一:如果以行动为结论,前提必须是意向对象么?这个对象是不是一个私人性的东西?这意向对象,在每一个事件中都是可以区分开的么?
回应:作者要挑战的就是这种观念,不是第一人称的就一定是内在的,不是物质对象一定是客观的,要有第三种道路,它反对的就是把行动知识当作心理状态。这个第三条道路怎么走,文本并没有完整的立场,但是突破口可能在购物清单的例子上,常识的命令本身不会被挫败,实践知识面对意向对象,意向对象可能没有成为物质对象,不能说我们没有非观察性知识了,可能是一种素朴实在论的立场。其实意向对象和物质对象并不是那么截然相分的,可能互相背离,也可能吻合,但是是两者不同的东西,是存在区分的,这种区分是由意义的。
提问二:实践知识的正确与错误的评价标准是什么?
回应:事件的出错不足以挫败实践知识,有可能陷入不可错的泥淖。但行动的知识不同于心理状态,可以由正确错误的区分的,它的错误也一定是意向对象的错误,而不可能是物质对象的错误误。实践知识的特点决定了行动的属我性,若没有把握到这个属我性或者属我性被搞错了,那么实践知识就出错了。
讲座在热烈的云掌声中结束。
(文/陈惠婷,图/蔡添阳)

 学校主页
学校主页 校内链接
校内链接 校外链接
校外链接 校内邮箱
校内邮箱




